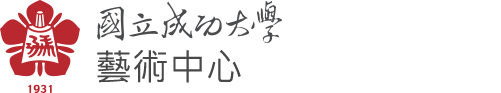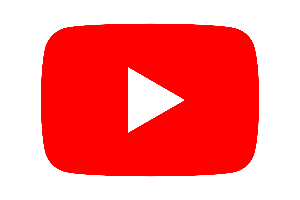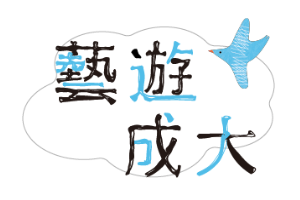最後更新日期
【藝文誌】河床劇團《被遺忘的》藝評 (112-1實踐課程-寫作篇)
河床劇團《被遺忘的》藝評
丁筠
當初在官網看到《被遺忘的》的劇照後,馬上就決定去看這齣劇,12/2 當天從台南一路搭火車轉公車,風風火火地趕到歌劇院,再匆匆找到中劇院進場。最後在我的喘氣聲和主持人的提醒中,觀眾和手語翻譯逐漸褪去,中劇院特有的極致黑暗襲來......
在黑暗中,斷斷續續傳來不屬於我的喘氣聲,燈光逐漸亮起,隱約能看到一位礦工正在推著一輛礦車前進,礦車連接到中央的黑色方柱,燈光隨著礦工的轉動跟著照亮他,接著第二位進場,接著三個紅衣舞女進場,接著一位紅衣歌女進場,唱著悠揚的聲樂,透過全景式敘事的方式形成一幅三足鼎立、詭異而優美的畫面。接著在舞台最前方亮起一列四盞燈,第一盞下站了一位穿著西裝、把玩著呼啦圈的男士,他將動物表演用的呼啦圈擺在礦工面前,上上下下地引誘著礦工一次又一次穿過圓圈,爬向一車煤礦,他們艱難地在狹窄的礦道裡謀生,在旁觀角度看來卻彷彿馬戲團裡的動物,盡在他人掌握中,只能走別人為他們規劃的路,不禁讓我思考,其實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下,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一位又一位的礦工呢?
好幾位親歷當年礦難的礦工都來到了表演現場,在表演後的會談中,他們說了一句我久久不能遺忘的話:「如果不是為了家人的誰願意去做礦工呢?」他們清楚地知道做礦工的後果,在舞台上他們不斷地攀上圍牆,努力地回到家,又努力地爬出牆去工作,最後身體被無數的穿著白袍的人抹塗滿黑色的碳末,被關進玻璃箱裡呼吸著汙濁的空氣,像極了在水煙中掙扎的害蟲,一點一點被侵蝕掉生命,呼救聲漸弱……。他們渴望保護的家庭也被腳下的地板包覆起來,與外界隔絕、無法逃離,而當他們終於被世人所看見時,他們卻被隨意的推放在檯子上,任由綠衣女人推著他們遊走、展示,圍觀的民眾彷彿都在為他們加油、吶喊,卻浮誇到虛假、令人惡寒,在得到了他們所想要的東西後,又紛紛心滿意足地離去。綠衣女人將礦工擺成面向觀眾的姿態,像一位藝術家又像媒體人般欣賞自己的傑作,彷彿礦工只是個人體模特。在失去人們的關注後,礦工開始跌落展檯,綠衣女人卻依然推著展檯遊走,完全不在意礦工的處境,在這陣荒唐的喧鬧後,沒有人真正在意他們。在真實世界中,他們的肺裡、嘴裡、指甲縫裡全都是碳粉,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四肢,即便如此,他們仍然在掙扎,在舞台上豎立一根一根細白的柱子,紀念著他們失去的一切,建立起一個營地,他們在裡面尋找、盼望、堅持,柱子倒了再扶起、倒了再扶起、被排列成各種陣列、變成像時針分針一樣旋轉、像計拍器一樣來回擺動,彷彿時間的流逝,最終他們放棄了,將柱子堆疊成溝火狀,埋葬他們犧牲的同伴。他們仍然回到傷害他們的礦場、繼續付出自己的生命,期待如此就能換取自己家庭的幸福與穩定,期待這樣他們的經歷就能被真正看見與記憶。他們掙扎,但是他們也逃避,劇中象徵資本主義的臃腫白衣人,在礦工經歷這一切苦難時,又提供給他們啤酒,所以他們可以忘卻,如同礦工大哥在會談中說的:「我們會在下班後喝酒,喝到像沒有明天一樣。」喝到忘記還有明天。
整體觀看下來表演者的動態感非常強烈,整個劇團的協作十分完美,他們把空間、舞蹈、打光等等複雜的元素簡化成一幅又一幅容易理解的圖像,演員的流動又將一幅畫構成拆散,再慢慢構成一幅新的畫面。每個畫面的轉移幾乎都在潛移默化中完成,讓觀者從疑惑到發現藝術家所想表達的,所有的細節會在一個新的畫面進行到三分之一時串連起來,彼此呼喚,形成一個緊密但隱蔽的故事邏輯。礦工被地板包覆即是其中令人震撼的一幕,這片地板布從表演的一開始就存在,觀眾早已習慣了它的存在,甚至都沒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卻在後續的表演中扮演重要的元素。對應了導演在會談中說到:「我們已經習慣了日常中人們為我們付出,觀眾看到乾淨的劇院實際上有許多人員在維護、工作人員躲在舞台側方和後方為表演付出,也是另外的一種礦工,而我們必須意識到這點,心懷感恩。」
很多人說自己不懂藝術,覺得藝術離我們太遙遠而難以理解共情,或是認為一些主題太過沉重,不願意給自己的生活加上更多負擔,便很少參與藝文活動。但我認為藝術來源於生活,任何事物到達一定比例或程度,就會變成人人都可以觸及或是感受到的美,有很多藝術是離我們非常近,也都是講述一些我們身邊的故事。這次河床劇團的表演就讓人覺得非常好親近,即使面對這麼壓抑的故事,河床劇團仍然能夠做到對一般民眾保持美感,整場表演不會產生令人抗拒的不適感,但又足夠強烈到讓我們能夠在腦海裡不斷回味,這對這件不可遺忘的事非常重要。他們的表演淺顯易懂但又引人深思,整場畫面的色彩基本上只有黑灰白、咖啡色、紅色、綠色,表演道具都是由柱、板、球體等共同組合成的幾何,加上精準無痕的燈光把控,他們靠著自己的美感與對故事的理解,掌握到某種潛意識裡的共同語言,如導演在表演後的採訪所言:「希望回家你們能夢到。」
表演時長一小時,卻讓人感覺偏向慢敘事,非常豐富卻能輕易進入到你的腦海裡,促使觀眾去反思去記憶,讓被遺忘的成為不可遺忘的故事。在表演結束後,導演、副導演、主舞以及一位親身經歷當年礦災的礦工大哥與觀眾進行了一場會談,這樣的安排,既與觀眾產生更多連結與聽幕後故事的機會,又給觀眾消化表演的時間。在走出劇場時剛好看到導演也一起走出來,於是鼓起勇氣詢問導演這樣的表演是怎麼構成的,是否有既定的劇本,導演十分親切有耐心地回答我並沒有,他們的創作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排練,用道具與演員的即興發揮去調整,包含燈光、音樂等細節都由所有人一起共同參與創作,因此每一次的表演也不會完全相同。一開始我聽到這樣的創作方式是非常震驚的,但仔細思考後其實十分合理,正是因為在熟知礦工的故事後,使用感覺與直覺去創作,才使得他們的表演能夠開啟人們的感官、觸動人心,所謂的藝術正是當藝術家發現一件微小的事,再透過他的創作不斷放大這樣的感受,使一般民眾可以感受到,引發世人思考,而河床劇團在這場表演做到了。最後謝謝他們送給每一位觀眾小小紀念品,我們都會記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