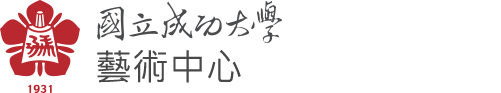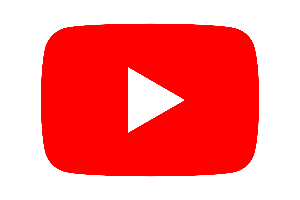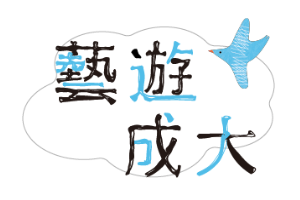最後更新日期
【藝文誌】骵II(111-1實踐課程-寫作篇)
骵II
詹景瑋
「用身體去體驗這件事情」是作者吳聯吟在此展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他在作品設計中保留了讓觀眾與作品互動的空間,希望「邀請」觀眾一同參與虛構與真實身體之間,兩個人的對話。
一進入展場便可看見一雙表示歡迎的手。
此次展覽以「骵」這個字為命名,作者吳聯吟說:「這個本裡面有一個木,就是我使用的竹木藤類的天然媒材;而本,則希望透過作品來探望我自己,內心本來的自己。」
這個作品以懸空的頭部及肋骨構成,當我們進入作品中以作品的視角向外看時,其實看見的是自己。作者在頭部內布置鏡面,讓本該向「外」看見整個展場的視角轉為看向「內」,呼應了以作品探望內心的初衷。
人在什麼時候最貼近真實的自己?是在夜裡緩緩將眼睛閉上任由思緒放蕩的時候嗎?
這個作品並非只是靜態的展現,而是會轉動的,在作品內部看著自己在自己視野中不斷旋轉,是否很好的運用虛構與真實的身體來展現出平時人們與自己內在對話的意象?
我們所見是否如他人所見?
當真實的身體與虛構的身體結合時,這個作品可以說是真正的完成。我們在完成的作品中看見自己,那一旁的觀眾看見的又是什麼?生活中我們不斷的認識自己,卻無法控制別人眼中所見的我們;我們在軀體中形塑自我,而眾人看見的卻是軀體被映照出的影子。我認為此作品的光影布置凸顯了這個特點。我們以虛構的身體往內探索自我的同時,無論虛構身體中的人如何改變,其延伸出的影子卻像他人眼中的自我一樣,看似毫無變化。
一種屬於台灣的雕塑形式
這個作品名為為旋轉。木料的材質很好地重現了手臂的樣態,以直向為主的材料紋理表現出血管攀附的效果。
作者吳聯吟將作品運送到展場的過程中,親自將「旋轉」穿戴在身上,並一路以旋轉前進的方式來走到展覽會場,模擬與廟會遊行相似的方式來表達這件雕塑所伴隨的概念。
「他是一種雕塑跟人,或者說是神跟人之間存在的一種,非常有趣又緊密的關係。」
廟會時,在神將搖晃身體的過程中落下的「篙錢」被視為平安符。並非民眾強取而來,而是必須藉由神將的身體搖擺使之自然落下後才能拾取。作品在旋轉行進的途中,向外開展的手臂營造出了神明「施予」祝福和民眾「接收」祝福的過程,也讓本為虛的神體與實的民眾互換呈現,十分有趣。「旋轉」無疑是連結神與人之間關係的重要角色。
此兩件作品可明顯看出是為了讓大眾體驗進入神將內部所設計的。
虛構的巨大身體,象徵著人們對於高位形象的敬畏與崇拜,而將之穿附於凡胎肉體上除了有「化身」之意,更可看出人們之於強大力量保身的渴望。除了台灣傳統文化外,在日本的影視媒體也能見到此類哲學。在岸本齊史所作的〈火影忍者〉中,有著名為「須左能呼」的強大技能。其能力為招喚出巨大的身體,依序以骨骼、肌肉、乃至鎧甲依序包覆於自身外,其巨大的虛構身軀可謂驅使著開天闢地媲美神靈的力量。而須左能呼這個名字的形象便是源自於日本傳說人物「素戔嗚尊」(或稱須左之男命),其最為著名的便是斬殺八岐大蛇的故事。
神將作為神靈在凡間的虛構身體,相信在信仰者的心中除了作為連結,同時也能作為如同須左能呼般以招喚力量的型態帶來安定。而卸除虛構龐大軀體的「脫殼」,是否可視為信仰者在虛構力量中超脫出更安定的精神力的一個過程?
此件作品位於展場最內部的位置,所佔空間相當龐大,同時表現出來的肢體意象也是最為抽象的。相較於其他作品的燈光是由外照射於作品上,其光源是由作品「內」部向外滲透出來。
如同前面的作品以虛實交會達到完整體現,繼作品與觀眾、作品與作者之後,此展覽邀請了台南在地不存在劇場的舞者古伊琳與這件作品共舞。其交織躍動宛若一名人類自地面向上向外迸發生長,向立體的空間衍生出額外的軀體。而位於作品內部的光源宛若這龐大身軀的「心」一般,隨之鼓動。
巧妙的是,同為作品與人、虛構與真實的身體之間的連結和對話,在不同作品中卻可以看見不相同的連結方式。位於展場空間另一側的作品呈現出了較為靜態的外至內的連結,正好與此以較強烈動態展現出的內至外互為對比。
我發現此次展覽裡的作品除了沒有明顯的頭部外,也沒有明顯的下半身。但在人進入作品後,就連結成了完整的身體,似乎透漏出了人於地,神於上的構圖。
而我在看過展場放映的前導片(youtube上可以搜尋的到)之前,我有先在展場內來回走過幾次了,木類材料與肢體元素顯而易見,但看過前導片後發現有些核心的概念是當下我沒發現的。動態展現的部分我認為是最難發覺也是最為可惜的,不論是作者吳聯吟身披旋轉一路模仿廟會遊行的方式前進還是舞者古伊琳與作品共舞的演出,都只能透過影片去欣賞,但同時卻又傳達了我認為此展覽裡最為中心的思想(廟會文化以及虛實身體間的連結和對話)。話雖如此,這搞不好也留給了我們一種獨自詮釋的機會。
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提出作者之死這個概念,認為作者在完成作品的那一刻開始,便與觀眾共享「詮釋權」,作者對其作品的創作理念也視為一種讀者詮釋。如果說作品與人之間的動靜結合構成了實虛身體之間的連結對話是「骵II」意象所要的終極展現,那在展場中只能透過絕大部分靜態展示去體驗的我們,是否獲得了另一條與另一個身體對話的道路?